文·武福廷
夜深了,刚刚秋季开学,王老师的窗口还飘着柔和的灯光,教室门前花池的杂草下,几只秋蛉叫的正欢,他还在批改全校22个学生的作业。今年,王老师是任教的第九个年头。

“王老师,王老师,我,我,我爹病了,俺娘让你过去看看。”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寂静的校园。
“小明,咋啦?你爹病啦!”王老师细声细语地问。
哦,他爹早就该死,只要在外不顺气、窝了火或是喝了几杯“尿水水”,不是找孩子的麻烦,就是打老婆,还闲茶饭赖,摔匙打碗是常有的事,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这个兔小子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早就该死了。
小明的娘———换弟,娘家为五,第六个孩子终于续起了烟火,常常一个人带着弟弟,与王老师一墙之隔,小时候过家家,换弟做新娘,许多半大不小的野孩子都想做新郎,一声粗壮的声音“我做她新郎,我做她新郎。”后来一道上学,一道割草,一道放羊,岁月长了,他两都大啦,村里公认的一对郎才女貌。要不是她娘和那个老不死的奶奶硬逼着她为多要些正价钱,她能跟那个“二混子”男人成亲吗?

崎岖的山路上,两个急促的身影在移动,明亮的秋月漂上了那三间破瓦房的脊檩,屋顶的几株蒿草清晰可见,山风阵阵,遍地的茅草呼呼作响。这美丽的山村景色,曾燃烧了多少他和她的青春欲望,年少的心,不知多少次飘飘欲醉,也埋藏了多少他和她的欢乐和憧憬。终于有一天,她给他跪下了,喃喃的一句话“对不起,我要结婚。”他抱头嚎啕大哭。后来他发奋读书,又编织着自己憧憬的梦,醒来时,月儿又照着这条崎岖的小路上。
... ...
她圆了家里的梦,区区几个小钱,为人妇,为人母。
他圆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梦,为人师,还是换弟儿子的老师,做了一位光荣的民办教师。
九年了,他也31岁了,再没有提起她的名字,可村里那些长舌头女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但隔着他和她之间的是一条茫茫长河。偶尔见了面难免也要打一声招呼。

九年了,他站在她的门外。
换弟打开了门,一个门里,两个门外。
他激动不安,她两眼扑簌。
“他,他还挺过来吗?”
她摇摇头,凄惨地说:“恐怕过不了黑夜。”
他们都愣愣地站在那里,死一样的宁静,好像这个世界像胶一样地凝固。
“王老师,想想办法,救救我爹。”孩子无助的声音,让人听得有点凄惨。
“等他死了,我们就结婚,我要养活你和孩子,我要待你好,和小时候一样,我要像样地让你过上女人该过的日子。”他急促地说。
她哭了,孩子哭了。
“他......,我就眼睁睁地看他......”
“可他,动不动就打你,骂你,还发酒疯,这样的男人,你......”
门“嘭”地一声关上啦,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月光照着他稍微有点驼着的背,一阵秋风骚乱了她的思绪,他的背影静静地印在门上。
屋内传来男人的呻吟声,又听女人小声说:“他爹,你再熬几天,等粜了瓜子凑齐了,带你到太原大医院看。”
男人有气无力的说:“我,我不行了,不要糟蹋钱,好好供孩子上学。”
女人无耐地低泣着。
门外,秋天的山风有点刺骨,月光好淡,王老师打了好几个寒战,虽说三十出头的人,头发花白,于屋上那几根蒿草,显得有点悲凉。
“哐当”一声,他不知用了多大的勇气,一脚踹开门,冲进屋里,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换弟和她的男人都吃惊地望着他。
屋里死一样的宁静。
他低下头,望着这个六神无主的孩子,“小明,现在就带你爹看病去。”
男人有气无力地说:“王老师,你打小就喜欢换弟,我不行了,不要糟蹋钱,以后她母子俩就全托付给你,你......”
他怒视着吼起来:“告诉你,往后你要再发驴脾气,小心我,饶不了你。”豆大的泪珠从这条汉子的脸上滚下来。
月光照着这条崎岖的山路,一个汉子,驼着另一个汉子,后边跟着他的女人和孩子......
后来,他离开了这个村,民办转正,到县城安了家。


图文:武福廷,繁峙县福连坊村。
编辑:冯璐
--END--
提示:若该内容侵犯您的原创权益,请点此通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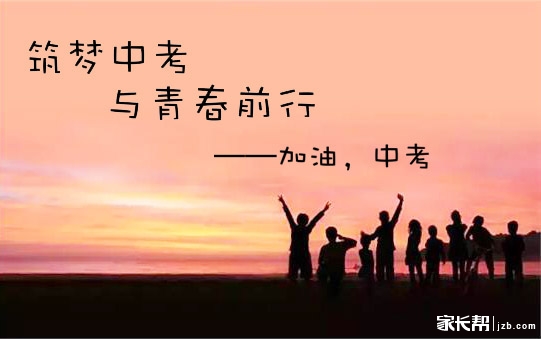





登录分享读后感、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