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凡八九十年代在砂河中学上过学的大营人记忆深处一定有一条磨灭不掉的路:从滹沱河桥南行一百米向西拐,下一段陡坡后便是一条笔直而宽阔的沙子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眼里),它通往大营火车站,是学子们去往砂中的必走之路,每两个星期往返一次,三年如是。
到砂河当然也有汽车,但我们只坐火车,一来省钱,八十年代大营――砂河只需五毛钱;二来时间对,十二点十分砂河往东,下午三点大营往西,到了学校不误上晚自习,在家的时间也可充分享受,两不耽误。那时住校生多,学校考虑到住校生回一次家不容易,想出个经济实惠的办法:两周合并过一次星期,过两天,在家住一晚(那时还是单休制)。每到第二个周五,一早上,我们这些要坐火车回家的人就格外兴奋,上教室前就把干粮袋拿了,放在桌仓里,心神不宁、度分如年地捱着盼着,第三节课下课铃一响,便抓起干粮袋冲向班主任室请假,有的班主任对哪些同学要提前离校了然于心,无需例行请假,仿佛已经形成“特权”:下学时间是十二点十分,火车到站时间是十二点零五,从学校步行到火车站需十五到二十分钟,坐火车向东回家的同学须得提前一节课离校,这成了多少年来约定俗成的规定。每隔一个的周五十一点半左右,便是我们这些前十一天缩在又黑又冷的宿舍啃又酸又硬的窝头、羡慕走读生回家吃好饭的人的出头之日,我们三五成群、趾高气昂地走出校门,不必在意校长老师的目光,不必接受门房老苑的盘诘。一出校门,我们就飞奔起来,归心似箭是此时此刻最恰当的语言。
半个小时的车程飞一样过去,下了火车走下高高的站台,一字排开等待我们的往往是推着自行车、伸长了脖子找自家儿女的父亲,我们这群“倦鸟”当然也在迅速对接,目光相遇时,满心喜悦的父亲不露声色地调转车头,欢欣雀跃的孩子跳上了后车座,父亲吩咐一句“坐好”,便飞腿上梁,回家喽!回大营的路是慢上坡,瘦弱的父亲努力地蹬车却还是要落后一截,到了快上桥那一段坡度大些,父亲躬着腰,使出全身气力一下一下吃力地蹬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夏天炎热时,我看到父亲穿着单衣的背上被汗水洇湿了,自责感从心底生出,但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屏住气往上提身体,拳头攥得紧紧的,用力夹住双腿,以期减轻父亲的沉重。去火车站是下坡便轻松了许多,虽然被又要度过难熬的两周的乌云所压,我还是好心情地晃动着自行车后座上耷拉下的两条腿,看看田野里的向日葵的笑脸,蔚蓝的天空下飞过的鸟儿,感受着大营一年四季特有的风。肩上的干粮袋鼓鼓的,母亲刚刚烙好的馍片不时飘出麦香味,混合着炒咸菜的葱油香。我紧紧地把干粮袋搂在怀前,生怕车子一颠给颠跑了,这可是我两周的生活补给,也是母亲省吃俭用、竭尽所能给女儿的物质精神食粮。
偶尔来接我的是哥哥,哥哥有的是力气,把自行车蹬得飞一般快,风在耳边呼啸而过,路在脚下“沙沙”地退后,我闭上眼睛听风,睁开眼睛看路,不用担心爬坡上不去,看着把别人甩后老远,心里说不出的惬意快活。路特别平坦的地方,哥哥竟然两手撒把,只凭脚蹬就让车子又快又平稳地前进着,我又紧张又兴奋,好像在亲身参与马戏团的飞车杂技,这种矛盾常常在哥哥长长的口哨声中结束。送站时哥哥会让我坐在前梁上,他则屁股离座,两腿直立着蹬车,路两边的田野、树木以火车般的速度飞驰闪过,我张开双臂,高兴地想:要是每次都是哥哥接送我多好!
遇上学校有特殊情况调礼拜,家里并不知道,我们便去离火车站最近的村子――西三泉的同学家借车,虽然饥肠辘辘,但能过一把骑车瘾还是很带劲的,一路上你追我赶,说说笑笑就到了家,在父母惊喜的目光中、忙乱的炒鸡蛋声中,美美地吃上一顿,简直觉得拥有了世间所有的美好,无比满足。
三年甚或四年五年,通往火车站的这条路承载着多少莘莘学子的理想,承载着几代父与子、母与女的梦想,承载着我们走出家乡看世界的野心,承载着我们的前程与未来。曾经多少人,走过这条路,几年寒窗苦,步入理想殿堂;曾经多少人,辗转往复,历尽沧桑,梦想不成真。无论如何,走过的路,终会留下脚印;付出的青春和汗水,终将不负你我。
时隔三十年,我的梦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境:我坐在旧式二八自行车的后座上,父亲一声不吭蹬着车,车轮碾过平坦宽阔的沙子路,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真好听,耳边风轻轻地吹着……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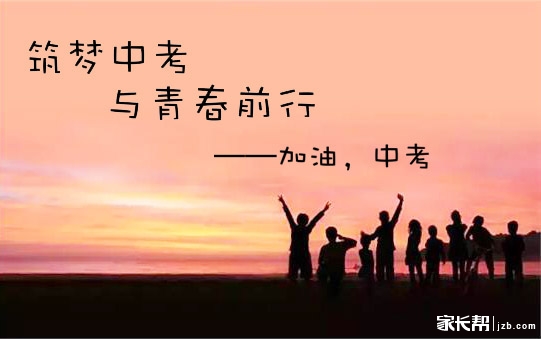





看过了,登录分享一下感受
或留下意见、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