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小兰
我这辈子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们沉默不语地抽烟、喝酒,特别是在寂静的黑暗中,总怀疑那袅袅飘散的烟雾和透明的液体里,隐藏着漫无边际的哀苦,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于是,心里面便会涌出一个唠唠叨叨诉说一番的愚蠢念头。不是因为寂寞。
不是。
从开始记事起,印象中的爸爸手指间便夹着一支烟,微笑着看我和小弟吵闹、游戏,那一缕缓缓升起的白烟,像爸爸伸长的手臂,环绕着我们,添几分安宁与快乐的情绪。
后来,发生了变化。1966年7月,妈妈突然离我们而去。把我和小弟带大的阿姨常常坐在厨房里,不煮饭,也不炒菜,两手捂着脸,压着嗓门哭泣。爸爸走过去,对阿姨讲:刘大姐,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接着,掏出烟,很用劲地划火柴。
天气很热,晚霞在街头巷尾投下一块块跳跃的光斑,辉映着墨迹点点的墙壁。爸爸还和往常一样,喜欢带我和小弟散步。只是少了微笑,话也少。即便是散步,他手上也夹着一支烟。我和小弟跟着他,单调地从宽宽窄窄的街上走过去,直走到小弟和我都感到腻味,好像心里有一只毛毛虫在爬。不散步的傍晚,爸爸就站在院子里的篮球边看打球,手里自然也夹着一支烟。
工作组找爸爸谈过几次话。谈些什么不得而知。回到家里,爸爸的话更少了。没有人安慰他。过去常来的客人几乎全都疏远了。现在,有时无意间想起那些没头绪的往事,便也能够原谅宽容当时令人心寒齿冷的疏远。那时,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况且其中还掺杂着自身难保的恐惧。
夜晚,每当一屋黑暗的寂静中,爸爸总是坐在藤椅里抽烟。烟头微亮的红光衬着他瘦削的脸。只几天工夫,他本来很白缺少血色的面孔变得蜡黄,皮肤像是也一下子粗糙、松弛了许多。除非烟抽得太猛烈,压抑不住爆发一阵猛烈的咳嗽声,爸爸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坐着,一支烟接一支烟抽下去。我躺在阳台上的小竹床上,望着满天的繁星,侧耳细听,真希望爸爸也能像阿姨一样哭泣,哪怕只哭一声。可爸爸——不。他只抽烟。
添几分安宁与快乐的白烟从此变得令人窒息。
关于妈妈,妈妈的死,爸爸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也许因为那一年我才14岁,难以懂得大千世界的复杂与世态炎凉。及至有一天,爸爸无意中看了我的日记,才对我说:“你妈妈是个好人”。接着又抽烟。停了许久,叹息:“总有一天你会懂得的”。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爸爸没说,仿佛所有要说的话都省略在那一支烟里了。
随后,阿姨离开了我们家。我们家也从那幢带卫生间、厨房、设备齐全的红砖小楼里搬了出来。低矮潮湿的工棚把生存的空间浓缩在一个极狭窄的天地里。这倒没什么。阿姨常说:“人没有受不了的苦。”我想,我也能像灰姑娘一样,干又脏又苦的活。让人难受的是那个飘忽不定的“心情”。好像每一天只剩下拉长的黄昏。
我心里淤积着排解不开的恐惧。时至今日还常劝小弟:“少胡说八道。”小弟笑我:“被整怕了。”也许,是这样。所以,苦苦地想把那一团无形的恐惧涂抹在白纸上。
当时,我不知道爸爸心里是否也淤积着恐惧,或者是思念母亲的悲凉?爸爸去世许多年以后,我才从与长辈琐碎的交谈中,慢慢地咀嚼出他的忧伤。其实,当他用微笑和一缕白烟给我和小弟安宁与快乐之时,心情便已很压抑。但毕竟亲子之情中还蕴含着几许天伦之乐。然而,男人所需要的并不仅仅只是天伦之乐。
爸爸病了。老病——胃溃疡。如果允许他去医院检查,总是便血一个十,两个十。不过,难得允许他去医院。唯一的宽大是允许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省报副总编的职早已撤掉,他天天扫街,写检查,批斗会也日渐频繁。
最初的革命风暴从心上过去后,所剩下的只是恐惧。我小心翼翼地给爸爸烤馒头片,用红枣和生姜熬汤,深怕有一天爸爸也会突然离我们而去。爸爸像是看透了我紧张的心绪,胃疼得抽紧,或者呕吐,从不呻吟,脸上还硬搬出一副笑容:“不要紧的。”手指哆哆嗦嗦又去摸香烟。
没有批斗会的夜晚,我便帮爸爸抄检查。许多年的风风雨雨,爸爸习惯于谨慎,每份检查必留底稿。我坐在靠窗的长桌前,像步入一个纷乱的成人世界。爸爸总是十分仔细地检查我抄下的底稿,用颜色浅淡的铅笔,一一标出漏字、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爸爸和妈妈一样,为人处世都恪守着一个古板的原则:认真。也许就是这种执著的认真原则,把他们推到生命的绝望之中。马马虎虎的人会把侮辱和对心的折磨看得平淡一些。
爸爸的性格多少有点变化,常想喝点酒,过去不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枯坐,也不要菜,一口一口呷下那透明无色的苦涩液体,然后一醉方休。胃疼得舒缓些,爸爸就求我给他买点酒 。昔日沉默的威严全部凋谢在孩子般急不可待的渴求中。因为他的胃,我只给他买红葡萄酒。爸爸得捱到夜深人静的时刻方可偷饮,自然毫无乐趣可言。
工棚的后窗对着一片荒芜的花园。秋夜的风冷冷地从枯草残叶上掠过,留下一些抖抖索索的声响。爸爸坐在后窗前,一杯酒,一支烟,悄无声息。我在黑暗中陪着他,总担心他喝多了,出事。只有小弟时起时伏的鼾声可以使爸爸的心情稍微好一些。偶尔,爸爸也会说起遥远遥远的过去,都是些我不大明白的事情。
那时,我根本不懂得一个人无可诉说的孤独与苦闷。我陪爸爸,是为了害怕失去他的恐惧。
也有酒后冲动、兴奋的时候,很少,印象中仅一次,好像和我带回来的那张报纸有关系。爸爸又想喝酒。爸爸没有活到1971年。不知道他读到有关9·13事件的详细报道,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时的报纸很热闹,标题总是触目惊心。我从不认真读报,只扫一眼标题了事。因为心中那团无形的恐惧,至今也没养成认真读报的习惯。爸爸则不同,不管在什么环境中,只要有报纸,他定会一字一句细细地读下去,仿佛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些别的东西。大概,这同他的职业不无关系。
夜晚照例不敢开灯。月光从后窗照进来。工棚里一层惨淡的白。报给摊在靠窗的长桌上,加大黑体字模模糊糊的一片,但仍散发着让人胆颤的气息。那张报纸上有一篇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
爸爸说:“狗屁不通!”
我惊奇地看他。烟头微亮的火光下,爸爸的脸上现出我不曾见过的极轻蔑的神情。
之后,便又喝酒。喝了好一会儿,爸爸又说:“像我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接着,脸转向我。我看到一点点红红的颜色和他眼镜片上闪闪的亮光。
还说了许多话,像一堆缠乱的毛线,我只记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什么的。不懂,也不想懂。
最后,爸爸走向已铺上棉絮的板床,很安稳地睡去。工棚里那一层惨淡的白似乎亮堂些,让人想到的不再仅是自己所处的境地。
可第二天一早,爸爸便又恢复了以往的沉闷和忧郁,胳膊上套着黑色的袖章,在篮球场的领袖像下履行每日一次的请罪仪式。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篮球上那一排低垂的脑袋和黑袖章,更让人感到被同类排除的恐惧。接下来,戴黑袖章者劳动改造,革命群众在篮球上学跳忠字舞。
工棚离篮球场挺近。激昂的音乐和歌声,像擂动的战鼓,震得窗上没安牢的玻璃都似乎微微晃动。我躲在狭小的空间里,既不想置身于欢乐的人群中,也不想看热闹。口很渴,拼命想喝水。我没有去看过爸爸劳动的情景。想像得出他随时会倒地不起的身体如何努力挣扎。我不知道,他请罪、劳动的时候可曾想到过酒后的慷慨难奈的话语。
如果,日子就这样持续下去,我想,爸爸会多活几年。爸爸说,回到家,只要看到我和小弟,能一块儿吃饭,便也就满足了。
终究不能。我要上山下乡。
走时,小弟正病着,高烧。爸爸烦躁不安地抽烟。头天晚上便把背包打起来了,很迟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等我醒来,爸爸已经做好早饭,手里握着半杯残酒。我急忙洗漱,饭却吃不下去。勉强扒拉了半碗烫饭。爸爸突然说:“记住,千万别谈恋爱。”声音嘶哑,语气却郑重。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没来由的叮咛。抬起眼睛去看爸爸,他却避开我的视线,将酒一饮而尽,然后缓缓垂下杯:“你走吧……”
也很想很快就走,将沉重丢在狭窄的工棚里,眼不见,心不烦,自欺欺人的安慰。爸爸倚在门边送我。他行动自由的界限就在那道门槛,除了请罪、劳动,不准逾越。即使没有人看守,他也规规矩矩地遵守。走出几步,我忍不住回过头去。爸爸还在看我,他伛偻着腰,眼镜却拿在手中,我猛地发现,爸爸深陷的眼睛里有泪。
不敢再回头,不敢用手背去抹自己的眼泪。那短暂而漫长的一刻,两辈子都不会忘记。不会。
乡下的日子不但苦,且单调。我比别人又多一分担忧:怕小弟病不好,怕爸爸突然离开我们。傍晚,从田埂上走过,去井里汲水,渐黑的暮色中总跳跃着一缕白烟、一杯红酒,伴着爸爸悄无声息的身影。
第二天秋天,秋收还未结束,没向队长请假,我和两个女同学决定偷跑回家。天还不亮,我们就踩着潮湿的泥地,快活地奔向田野,将一个又一个雾霭中的朦胧的小村庄丢在身后。来到公路时,太阳早已升起,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可我们谁也不愿花一分冤枉钱,买票乘长途汽车。心虚地同时扬起手臂,在路旁拦车。一辆运送长竹的卡车终于停下了。我们趴在堆得高高的长竹子上,身体也随着长竹上下跃动,很危险的。那时却浑然不觉,还相互庆幸好运气。
久违了,城市。及至看到从工棚里透出的灯光,我的脚步才不由得迟疑了一下。
灯影中,爸爸正在弯腰清扫炉前的煤灰。看见我,先是疑疑惑惑地一惊,立刻就又万分高兴,手忙脚乱地拉开抽屉找钱。和从前的镇静自如相比,判若两人。又要我给他买酒。要白酒。爸爸叮嘱我。
我上街买酒时,专政队把爸爸叫走了。小弟野跑了一天,很累。和我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脏兮兮的。嘴角、鼻翼,有几处明显的抓破的伤痕,血和灰混在一起,凝固了,像涂了一脸暗色的酱油。不用说,也知道别的孩子为什么欺辱他。我关了灯,坐在黑暗中等爸爸。
天阴着。看不见后窗外的星星和月亮,也听不见风雨声,虽然已是秋天,却有点儿闷闷的热。我也伏在长桌上睡着了,直到轻微拉灯声将我惊醒。爸爸正在解绑在膝盖上的棉花垫子。他的两个膝盖都跪肿了。我想赶快用温水给他擦擦,爸爸却摆摆手,眼神愣愣地看着小弟的脸,颓然地低下头,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烟。
爸爸没吃我给他买的豆腐干、茶叶干,只喝酒。他说不想睡,想和我说一会儿话。
“像我这样的人真不该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该要孩子,是我害了你们,还有——你妈妈。”
很静的深夜里,爸爸的声音仿佛在狭窄的四壁间回荡,悠远、深长。他把脸转向小弟的床,又默默不语。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一缕白烟缓缓升起。
“给你写了一封长信,寄不出去,就又烧掉了。也没写什么,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这一辈子,于国于民问心无愧。”
语气里凝聚着漫长岁月的愤怒与叹息,转而却又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琢磨不透他这话的实际意思。
爸爸能告诉我的,都告诉我了。包括那一段压抑了他大半辈子的“历史问题”。那是他们那一代人中,一个19岁青年的曲折经历。仅四个月,两代人洗刷不清。现在回过头去看,并没有什么让人心跳脸红的,良心不安的事情。
一夜没睡。我和爸爸在黑暗中睁眼坐到天亮。很早,我便离开了家。因为专政队不允许。
没过几日,爸爸便去世了。他像妈妈一样,自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并不怎样漫长的一生。那是1969年,爸爸享年50岁。
小弟和在北京长大的哥都不沾烟酒。他们和我一样,有意识远避烟酒。因为烟和酒系着爸爸的瘦削的身影,也系着那一段永远让人无法忘怀和原谅的耻辱岁月,还有自心的囚禁——恐惧。
(原刊于1989年《文汇月刊》第4期)
附语:
大前年,我读到当时安徽四家店之一施培毅叔叔的回忆录,方知我爸爸并非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死于非命,因被专政队殴打摧残,吐血,得不到医治而离世。父亲去世那一天,专政队当晚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我年仅15岁的弟弟被强制到会和已经去世的父亲一起挨批斗。而我那时还在长丰的生产队里。弟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一次偶然从别处得知,忍不住号陶大哭。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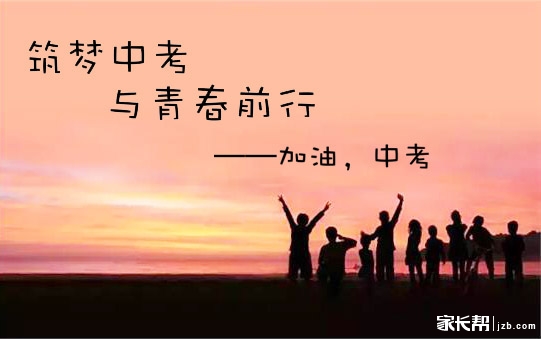





看过了,登录分享一下感受
或留下意见、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