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钱文辉
我们这帮老北大学子,不管日后是幸运者还是命运坎坷者,都把考入北大认作前半辈子最好的人生选择(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校园里处处可见“青春无悔”“无悔作北大人”的标语牌,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因为在北大学到了真学问,夯实了知识基础,学到了不人云亦云的脾气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而这和业师们在教学上求实、民主的作风大有关系。
系主任杨晦在我们大二末、大三初时负责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学科,杨先生特别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反复说明“文学专业化的要多学语言,语言专门化的要多学文学”,要同学们学得博一点。当时同学们特别是分到文学专门化的同学有点想不通,质问杨先生:方言学要学国际音标,音韵学要学古无轻唇音之类,这对文学有何用?更有一位同学S君在文史楼里贴出了一张漫画:一只大公鸡两爪分开,踩在一个汗水淋淋的学生两手托着写有“语言”“文学”字样的两大堆书上,标题为“有鸡联系”,以之向杨先生发难,当时还有不少大字报也针对“有机联系”而来。杨先生为此在我们年级开座谈会,会上又反复解释他的“有机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们在各自的事业中都尝到了杨先生“有机联系”的甜头,不少人成为专才兼通才,既拿得起文学,又拿得起语言,甚至历史、哲学,成为教育界、学术界著名的多面手(就是那位画漫画的S君,目今也成了国内颇有名望的“杂家”了)。杨先生作为系主任,视野极为广阔,给我们年级设置的课目涉及方方面面,我们入学后第一学期,就一下子给排了八门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引论、人民口头创作、形式逻辑、马列主义基础、俄语、体育。我初步统计,在大学五年,除这八门课外,我们还学了中国文学史(先秦至近代)、现代文学史、中国戏曲史、汉语史、汉语诗律学、音韵学、文字学、汉文学语言史、语言学理论、文艺学引论、中国文艺思想史(未讲完)、美学、汉语方言学、工具书使用法、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西洋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联共党史、英语、德语(选修),还有《红楼梦》《聊斋志异》《文心雕龙》《鲁迅》等等的专题讲座,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全国最知名最有发言权的教师。还请周扬、刘白羽、邵荃麟、何其芳、冯至、曹靖华、朱光潜、蔡仪、翦伯赞、冯雪峰、冰心等讲文艺规律,讲美学,讲文学创作,讲历史,讲外国文学专题等。同学们毕业时因学了这么多课而感到满足和骄傲,有人夸言道:我们是知识武装到牙齿走出北大的。
游国恩先生讲先秦文学,他是国内这一段文学史的权威,他讲课十分扎实,边讲边发参考资料,《诗经》《楚辞》的参考资料就发下厚厚一大本,叫我们认真自学。他是我国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对《楚辞》的要求自然更严格,课堂上对《离骚》逐句讲解,还作周密考证,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游先生带着常见的笑容,用时有齿音的江西口音背诵《离骚》开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降读“红”音)……”的神态。他详细论证他的观点:届原遭两次流放,“离骚”即牢骚之意。他讲“摄提”格,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工整的“十二辰”图,并引王逸、朱熹的言论解释“摄提”所指的屈原出生的确切年月日,……这种种情景,如今均历历在目。他要求学生背诵373句2490字的《离骚》全文,我们白天背、晚上在熄灯后躺在床上也背。游先生考试用口试形式(其他不少先生如高名凯也用这种形式),在会场里放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他和两位做记录的助手,坐在一边,考生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和他面对面。题由考生当场从一只纸盒里抽,记得我抽的题纸上有三道题,其中一道就是一大段《离骚》的背诵,我因为早已背熟了,圆满完成,另外两道题也回答出来了,并且经受住了游先生的补充提问,游先生当场批我“5分”(当时学苏联五分制)。这种酷似三堂会审模样的口试方式,实打实,绝不可能出现如今在大学里时有发现的那种作弊现象。我们年级在五年里也没有听说过谁做过作弊这种不光彩的事。
游先生在课堂上时常告诫学生研究学问要按孔子的古训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把“知”“之”都念成“底”的音,我们觉得滑稽,课外开玩笑学着念“底底为底底”,并趣称游先生为“底底先生”(属大不敬)。后来学了音韵学,才知游先生念的是孔子当时的上古音,上古无舌上音,知系读端系。游先生引孔子古训是一种求实精神,但先生学富五车、博闻强记,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不知”的。年级里有一位I君曾在课间向他请教“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出典,游先生随口答道:“在《韩诗外传》的一条注里”;我本人在1959年参加年级修订编写《中国文学史》(四卷本)时,分在游先生指导的一个小组里,有不懂的典故请教游先生,他总是能给我满意的答复,但又总要跟上一句话:“你自己再去查,看看对不对。”1958年大跃进,吹牛的风气也刮到了我们年级,什么“集体写超过《红楼梦》的小说”啊,什么“十年出一个鲁迅,五年出一个郭沫若”啊,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啊,有人放出“快速赶超游国恩”的豪言壮语,系主任杨晦先生听到后批评道:“你们在学术上二十年能赶上游先生就算不错了。”确实,游先生功底厚实,给我们学子树立了如何扎实做学问的榜样。
魏建功先生上《古代汉语》《汉文学语言史》课,发下大量古籍原文,但不加注解。当年一位学习班长代表同学要求他作点注释,魏先生加以拒绝,正色道:“读古书要下死功夫、笨功夫,不能走快捷方式,也没有快捷方式可走。老把注释作拐杖,将来离开拐杖,不是连路也不会走了?”魏先生的求实作派还表现在他的“付之阙如”的传统治学态度上。大一下半学期魏先生讲古汉语文选北齐的《洛阳伽蓝记》,他采用逐句讲解形式,讲到一处,突然停下,说:“这一句我不懂,讲不了,怀疑有缺字”,一级教授,也有不懂且坦诚说不懂,这让我们大受震动,这是一次难忘的求实作风的言传身教。
王力先生讲《汉语史》《汉语诗律学》,黑板上文图并茂,列出的韵图表,古今声韵调变迁规律,近体诗的对黏、拗救,严密细致,像在讲数学课开列数学公式。他既有画蓝图、搭架子的巨匠的气魄(他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多门学科的开创者),又能细针密缝,一丝不苟,处处表现出求实的科学精神。王先生也很注重“付之阙如”的治学态度,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特意讲了一则他的业师王国维在讲古籍时跳过几段说“自己不懂,讲不了”的故事,并指出这就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周祖谟先生是著名的古音韵专家,但他给我们开的是《现代汉语》和《工具书使用法》。一口标准、动听的普通话(他领我们读四声例字“中国解放”“生活改善”“积极努力”,简直像在唱歌),一手整齐、娟秀的粉笔字(连旧式国语拼音字母也写得十分漂亮),带头写规范的简化字,每次上课都发练习题,常常教导我们多读经学古籍,打下基本功……周先生时时处处给同学们一种求实的印象。
高名凯先生第一学期就给我们开难课:《语言学引论》(普通语言学),他是我国这门学科的开山祖。我当时在图书馆里翻阅旧燕京学报,见他发表的语言学文章很多,深奥得看不懂。他在国外声誉也很高,50年代中期他到波兰科学院讲学,全场起立鼓掌,该国报刊上也作为重要新闻。他讲的普通语言学,涉及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所以他特别注意用大量中外语言例证来说明问题。用中文作例,我们听得懂,也最欢迎,如他讲词与词的语义关系时,用“红烧肉”一词为例(他福建口音重,“红烧肉”念成“逢烧肉”,至今同学们忆起高先生,必然忆起“逢烧肉”),用英文的例子还可以明白,但他还用法文、德文、印度梵文、阿拉伯文等作例,这就让我们如坠“五里雾”中了,但也就此让我们学到了“孤证不为证”的学术求实精神,对日后自己开展研究时如何广积资料很有启迪.
林庚、吴小如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中的两位,现在年届八九十,是国宝级人物。林庚先生讲课注重艺术形象的分析,而且落到实处,注重用作品语言本身去分析形象,令人信服。记得林先生在讲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后,课堂上时间还有富余,他就以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为例子,讲“木叶”和“落木”中“木”的形象。说“木”与“树”在逻辑概念中是相同的,但在诗歌语言中,诗人们都要尽量利用其逻辑概念相同以外的其他不同部分。一提起“木”,就很少想到树叶的形象,只是光秃秃的树干一根。“午阴嘉树清圆”,就只能用“树”,用“木”就不能使人联想到叶的清荫。所以,“木”是用来描写辽阔、稀疏天地的最佳形象,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黄庭坚的“落木千山天远大”就是如此。林先生进而又说“落木”与“木叶”的区别:前者没有叶,后者还有些叶的形象,故“无边落木”与“落木千山”就最能逼真地传达出严秋的萧瑟;而“洞庭波兮木叶下”,则带有叶子似断非断的形象,这样,“袅袅兮秋风”就更有缠绵之情。林先生说“木”,深入到了语言的骨髓里去分析诗歌的形象,通过具体细密的分析,发掘出古典诗歌字形修辞这一未被发现的特点。直到现在,学子们谈及林先生的务实精神,必举此“说‘木’篇”。
吴小如先生讲宋元文学史,这位旧清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当时才三十六七岁。安徽籍贯却操一口纯正的京白,上课精神饱满,发音洪亮(去年在北大听先生讲话,依然如此),诗文、戏曲、小说、训诂、掌故、经学门门精通,在周三全校京剧欣赏会上,还能有板有眼唱京戏,他广博的知识、坚实的学问,使同学们极为佩服。当时他还只是讲师,系里讲师而能上课堂讲主课者,属凤毛麟角,在我心里,要不是北大盖子多(教授多),他完全可以评上教授。他与游国恩、林庚、冯钟云、吴组缃、季镇淮诸教授共同担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6个段,这要有真功夫才行。吴先生非常负责,讲了一个阶段后要叫学生把听课笔记交上去让他检查。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用红笔批了“详细”两个大字,这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不仅有求实精神,当时教学民主空气也很浓,不同学术观点的先生们在课堂上展开争鸣。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宣传他自己的“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实词无词类可分”的观点,而王力、朱德熙先生则把在学术刊物上与高先生的争论,延伸到课堂上;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主张薛宝钗属反面人物,而同时请来讲《红楼梦》的何其芳先生则认为薛是封建主义的牺牲品,不是反面人物;请来朱光潜与蔡仪对讲美学,朱先生认为美是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而蔡先生则认为美是纯客观的;杨晦先生一贯反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传统公式,写文章申述,在课堂上也申述,这种独立思考、决不泛泛而论人云亦云的精神对学生很有感召力,连我这个一般不愿在公开场合讲话的人也为先生摇旗呐喊起来:1959年4月,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关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问题论纲》,系统地批评了那个公式,适时正赶上我们年级要修订编写《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在一次师生共同参加的编写讨论会上,我发表了一大通反对此公式的理由,建议“解放”一大批像陶渊明、王维、李贺那样的古代作家,会后听班干部转告,我的发言得到了在座几位先生的好评。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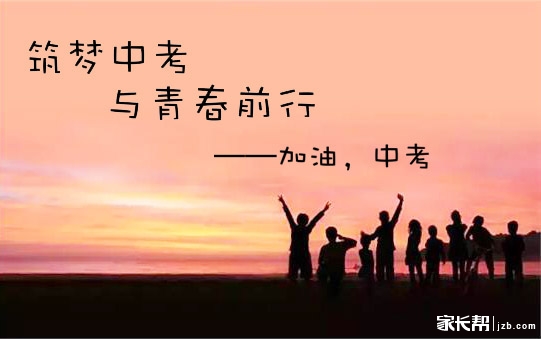





看过了,登录分享一下感受
或留下意见、建议吧~